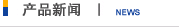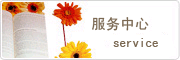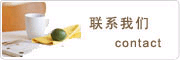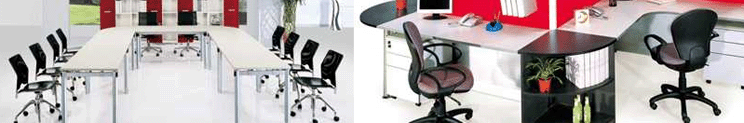

网站公告
办公家具-一个乡村小木匠如何成为大都市的家具设计师
作者:无
出处:无 加入时间:2009-11-09 10:42 点击数:次
一个乡村小木匠如何成为大都市的家具设计师?“如果没有百姓生活的富足,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50多岁的田艳波这样描述自己的从业经历,“是新中国的变迁成就了我的设计师梦想”。
“没有人们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就没有我这个小木匠这么大的天地,是越来越富足的生活成就了我的设计师梦想,我们是被时代赶着走的。”记者见到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厂设计总工田艳波时,他这样向记者慨叹。上世纪70年代,在河北衡水初中毕业的田艳波给自己做了第一个人生规划,要做一个靠双手赢得邻里称赞的木匠,那一年,田艳波开始跟村里的木匠学做农村木工活,一年后,他离开老家,投奔到二哥所在的延安,十多年里,田艳波为学木艺,辗转于陕西、河南、安徽、黑龙江等省内各区市,从一个乡村的小木匠渐渐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为城里人做高档家具的能工巧匠,直至成为享有盛誉的家具设计师。
为受尊敬——立志做乡村木匠
1966年前后,打家具都得请木匠
1966年,11岁的田艳波跟随父亲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河北衡水,开始了边学习边做农活的生活。初中毕业后,田艳波为自己的人生拟定了初步计划——做个受人尊重的木匠。他在村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师傅,开始学习简单的农用木工活。田艳波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做个木匠可以为邻里乡亲帮帮忙,每天有好的饭菜吃,受到邻里乡亲的敬仰,这样的感受不仅仅是来自于他对周边生活的观察,也来自于他有个做木匠的二哥,通过亲人的描述,他感觉做个木匠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
跟着师傅走东家奔西家,田艳波只是做些简单的农用木工活,比如做个凳子、门窗、耕犁、大马车、风箱等,完全是出于满足农民实用需求去做一件家具,从没想过要有所突破。事实上,田艳波的这段初始从业经历正是此前一二十年中国家具生产现状的真实写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谁要想用个家具都得请木匠手工打造,很少有人能直接买到成品,所以在那个时代,作为手艺人的木匠能被人另眼相看。木匠的本事就是将师傅传授的绝活原封不动地再现,重复不断地为每个家庭打制同样的家具。
在家乡做了一年多的农用木工活,田艳波有了新的思考,家乡不仅木材资源匮乏,且农民木工活需求有限,木匠手艺一般,留在家乡不是长久之计,应该走出去,到木材资源充足、木工活需求大的地方学习给城里人做家具。
四处学艺——进城偷偷摸摸干活
1966-1978年,限制乡下人进城谋生
1971年,年仅16岁的田艳波离开了家乡衡水,只身前往延安,他希望自己的收入和技艺在那里有所收获。在延安待了一年,1972年,田艳波辗转到了西安,那里是二哥做木匠活的地方,他开始大量接触打制城里家具的木匠,并为自己选了一个手艺精湛且十分严厉的师傅,师傅门下弟子众多,但田艳波是惟一一个学得师傅全部手艺的人。在西安给城里人做了三年家具,田艳波是充实的,也是心酸的,“虽然学会了做城里人用的家具,开始有了自己的收入,但很少有吃饱饭的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地人,能拿到的粮票很少,最重要的是,经常有管事的人儿来查,要是被查到就要被送回老家,几年里,感觉一直是在躲避中生活”。
1975年,经熟人介绍,田艳波起身前往郑州,在河南省纺织机械厂木工组里当起了工人。从一个流浪的木匠变成工厂工人,田艳波的心总算感到了一丝安稳,初入木工组,从钉设备货箱板子开始,田艳波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木工人员的素质,很快被分到了木工组做家具的队伍中,开始给工厂下边的宿舍和宾馆做家具,这让田艳波练就了一辈子从事家具制造工作的基础。“木工组制作家具的队伍时常超编,为控制人数,领导每几个月就会举行一次比赛,谁做得又快又好,谁就留下,经常排在后面的人就被送走。”前几次比赛,田艳波还不算出色,后来几次,他总是排在前几名,成了组里非常出色的木工。“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一个月能拿60多块钱,相当于国家规定的四级工的工资,领导特别欣赏有技术的人,所以那一年我过得很开心。”
在工厂里为宿舍、宾馆做家具是比较规律的,任务量也大,这除了让田艳波练就了一身本领,也让他对打制家具有了些新思考,“那时的家具造型非常简单,到现在人们还能在某些老房子里看见那个时代的家具身影,最多的就是‘文件柜一头沉’”。田艳波指着龙顺城技术科办公室内放在角落里的一个文件柜对记者说,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最流行的家具,一般比较宽裕的家庭或有身份的人家要打家具,或者是工厂为某些单位批量打制家具,必然会选择这样的文件柜,如果再要配上一张书桌,那就一定是“一头沉”,就是一边有抽屉,一边只是桌子腿的那种书桌。“经过打造者几年的思索,家具在款式上有了一些变化,而且在种类上也稍微丰富了一些,出现了高低柜、小衣柜、五屉柜等家具,这些家具款式曾风靡一时,现在在一些单位的老房子还能看见这样的家具。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样式能十几年不衰,跟人们的信息相对闭塞有关。”
返京待业——创业得到家具厂赏识
1978-1990年,外企进驻带来设计风潮
1978年2月,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严寒逼人,田艳波离开郑州来到大兴安岭一年有余。当时的田艳波有两个“一生的梦想”,一个是去南部的热带雨林,一个是去北部的大兴安岭林区,两个地方都有丰富而珍贵的木材,这对一个木工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源。离开郑州的时候,田艳波试着先往南走,但走到安徽地界,那里的方言他就基本听不懂了,于是当即掉头北上,到了大兴安岭地区。在大兴安岭的一年多时间里,田艳波感到无比的惬意,每个月他可以仅凭打家具就赚得300多块钱,这相当于当时一个省长的月收入,周围还有一些欣赏他的朋友在照顾着他。“那一年多是我最自豪的岁月,我时刻感觉自己是个有钱人!”
虽然在外面游刃有余,但每到过年的时候,田艳波会觉得很苦涩,家家亲人团聚,而他只能在街角火车站里徘徊。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1978年年末,父亲被允许回到北京,随后田艳波便回到了北京,成为了众多待业知青中的一员。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田艳波没事就往天坛街道劳资科跑,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最后工作没等到,倒是与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及一些从全国各地返城的知青熟悉起来,直至组建了一支木工队接零活打家具,“那个时候每个月也可以收入300多块钱,日子过得挺好,还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说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坐在家中等饭’的好模范,北京电影制片厂专门针对我们的事迹做了‘创业模范待业青年’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一阵好评,木工队从最初4人发展到28人”。
技艺娴熟的田艳波引起了一个“奇怪老人”的关注,每次田艳波干活的时候,他总是远远地蹲着看,看了两个多月,老人走过来问田艳波愿不愿意到北京硬木家具厂工作,提到“硬木家具厂”,田艳波的脑中马上闪过“有好木料”这几个字,作为木匠的田艳波对木料的偏执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老人,最后老人承诺“如果你来就让你当工厂画线的”,在这样的诱惑下,田艳波兴奋地到了北京硬木家具厂。“画线的是木匠中手艺最高的,俗称‘掌作儿的’,是工厂生产车间里‘领头的’,只要在来料时画上在哪里打眼,打多深,其余的就分配给其他木工做。”看中田艳波的老人就是北京硬木家具厂机加工部门主任,在画线的岗位上田艳波一干就是7年。
这7年让田艳波对家具设计有了更深的思考,什么样的样式更美观、更省料,能让家具结构更稳定,对工厂里每个新到的家具图纸,田艳波都会目不转睛地盯上半小时,他在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去设计这个家具”,设计的概念在那几年中时刻在田艳波的脑海中闪现。1987年,田艳波的职位从一个“画线的”变成了“出样的”,身份从一个工人变成了技术人员,被工厂派到外面参加“家具制图培训班”学习,从此成了北京硬木家具厂里的头号设计师。“出样的,就相当于一个大掌柜,客人描述要什么样的东西,你得能给画出来,然后再叫徒弟们去做,大掌柜的经验全凭亲手操练积攒起来的。”
正是田艳波走上“出样的”工作岗位的那几年,中国家具制造领域开始有了“设计”这一概念,田艳波也就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称得上设计师的群体中的一员,开始对设计有了更多的追求。“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国外企业已经进驻中国,对当时中国的城市生活起到了不小的改变作用,这对家具设计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大大小小的家具展销会上你会发现,家具款式设计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家具生产上开始使用五金件,这对家具设计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古为今用——钻研明清家具技艺
1990-1997年,家具式样越来越洋气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家具制造领域迎来了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时代,广东、浙江等地产的家具输送到全国各地,家具不仅价格便宜,款式更是新颖多样,多数款式是老百姓以前从未见过的,百姓居室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得益于大型工厂化生产的家具制造企业从国外引进生产设备的同时,也一并将国外的家具款式直接“引进”,家具制造企业在设计上完全奉行“拿来主义”,这无论对工厂还是对百姓,都是一个不错的举措。
新兴的工厂化生产的家具制造企业对老牌的国有家具企业造成的冲击不小,田艳波所在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在1993年更名为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厂,生产重心转移到了古典红木家具制作上,继承了“龙顺城”这一明清家具老字号招牌,田艳波开始大量研究明清家具的制作技艺,与实行“拿来主义”的现代家具制造企业相比,龙顺城和田艳波走上了一条通往艺术殿堂的艰难道路。
在研究明清家具的几年中,田艳波对家具设计的思考变得复杂起来,想要再现明清家具的真实风貌,必须见到大量的明清年代的真品,但这些真品只有倒卖古董家具的“倒爷”才见过,而他们又不会制图;研究古典家具的专家学者对明清家具风格和雕工技艺会有准确的鉴别能力,但他们没有实践,做不出来家具;拥有绝佳技艺的匠人们一代代故去,他们的手艺逐渐失传。要想制作出韵味十足的明清家具,不将这些“权威人士”聚集起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将明清家具的精髓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
田艳波在明清家具研究道路上的苦恼没有对现代家具制造企业的飞速发展造成丝毫影响,行走在设计“拿来主义”道路上的现代家具制造企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销售高潮,生产企业数量也在几年之中向千位数字迈进。
专职设计——追求中西结合的风格
1998-2009年,市场对原创设计需求强烈
大量的家具生产企业为城市和乡村的居室生活添上了亮丽的色彩,1998年前后,随着住宅房屋商品化,人们强烈改变居室生活品位的需求催生了大量家装公司的出现,由此“家居设计风格”这一概念浮出水面,人们对家具设计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也正是这一时期,部分大学专业中出现了“室内装潢设计”这一专业,这说明家具生产企业对设计的需求已经十分强烈了。
看到了家具销售受制于家具款式设计,家具生产企业老总开始频频造访国外家具设计博览会,将国外的样品和新品家具宣传册带回国内,依葫芦画瓢地照样生产,由此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国外家具设计展禁止中国人入内”的不光彩事件。中国家具市场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大批国外家具生产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1999年,田艳波带着多年对中国古典家具设计的研究成果离开了龙顺城,到了一家在中国设厂的瑞典家具生产企业从事家具设计工作,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田艳波成了公司的设计主力,多个设计作品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赞扬,由此得到公司老板大为嘉奖,“公司的很多大客户都是响当当的跨国公司品牌或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我们要为他们设计所有的办公家具和各场所用家具,通常我们要给出他们一个中西风格结合的设计方案,这样既符合这些公司的国际北背景,也适应了他们立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田艳波的成功说明市场对家具原创设计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也就是说,家具设计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意识到家具设计价值的中国家具制造企业已经开始愿意在设计上加大投入,近几年来,驰骋中国家具市场的曲美家具频频与国际设计大师接触,付高额设计费请他们为曲美设计家具,曾有国内家具厂愿意出30万元购买曲美家具的设计图纸,但曲美家具并没有卖掉自己的设计作品。就连老字号天坛家具也开始花巨资邀请国外设计师担纲设计,使产品系列极大丰富,一改往日单一沉闷的设计格调,出现了美式、中式、现代等多个风格的系列产品。
2001年重新回到龙顺城的田艳波目睹了这几年中国家具设计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家具设计市场的强烈需求令田艳波感到欣喜。现在人们都追求生活品质,家具设计除了要满足基本需求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求与众不同。为此,田艳波也为市场不能培养和提供一批与需求同步的中国设计师而哀伤,“虽然大专院校提供了室内设计专业,但走出校门的设计师往往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因为他们太缺乏动手的经验,很多的设计只能停留在纸面无法落实到生产上,由此导致很多企业宁可花钱到市场上买成品拆了研究,也不愿意付费请设计师,企业的不付出造成了中国设计师成长慢,同时,设计师不肯潜心研究、难耐艰苦生活、抄袭成风也使其自身成长缓慢。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家具企业可以十分慷慨地为设计付费,而中国设计师也愿意为自己的名字负责、仅凭‘某某人设计’就能赚钱,到那时,中国家具设计就真正形成产业、走向成熟了”。
“没有人们高品质的生活需求,就没有我这个小木匠这么大的天地,是越来越富足的生活成就了我的设计师梦想,我们是被时代赶着走的。”记者见到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厂设计总工田艳波时,他这样向记者慨叹。上世纪70年代,在河北衡水初中毕业的田艳波给自己做了第一个人生规划,要做一个靠双手赢得邻里称赞的木匠,那一年,田艳波开始跟村里的木匠学做农村木工活,一年后,他离开老家,投奔到二哥所在的延安,十多年里,田艳波为学木艺,辗转于陕西、河南、安徽、黑龙江等省内各区市,从一个乡村的小木匠渐渐成长为一个技艺娴熟、为城里人做高档家具的能工巧匠,直至成为享有盛誉的家具设计师。
为受尊敬——立志做乡村木匠
1966年前后,打家具都得请木匠
1966年,11岁的田艳波跟随父亲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河北衡水,开始了边学习边做农活的生活。初中毕业后,田艳波为自己的人生拟定了初步计划——做个受人尊重的木匠。他在村里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师傅,开始学习简单的农用木工活。田艳波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做个木匠可以为邻里乡亲帮帮忙,每天有好的饭菜吃,受到邻里乡亲的敬仰,这样的感受不仅仅是来自于他对周边生活的观察,也来自于他有个做木匠的二哥,通过亲人的描述,他感觉做个木匠可以让自己衣食无忧。
跟着师傅走东家奔西家,田艳波只是做些简单的农用木工活,比如做个凳子、门窗、耕犁、大马车、风箱等,完全是出于满足农民实用需求去做一件家具,从没想过要有所突破。事实上,田艳波的这段初始从业经历正是此前一二十年中国家具生产现状的真实写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谁要想用个家具都得请木匠手工打造,很少有人能直接买到成品,所以在那个时代,作为手艺人的木匠能被人另眼相看。木匠的本事就是将师傅传授的绝活原封不动地再现,重复不断地为每个家庭打制同样的家具。
在家乡做了一年多的农用木工活,田艳波有了新的思考,家乡不仅木材资源匮乏,且农民木工活需求有限,木匠手艺一般,留在家乡不是长久之计,应该走出去,到木材资源充足、木工活需求大的地方学习给城里人做家具。
四处学艺——进城偷偷摸摸干活
1966-1978年,限制乡下人进城谋生
1971年,年仅16岁的田艳波离开了家乡衡水,只身前往延安,他希望自己的收入和技艺在那里有所收获。在延安待了一年,1972年,田艳波辗转到了西安,那里是二哥做木匠活的地方,他开始大量接触打制城里家具的木匠,并为自己选了一个手艺精湛且十分严厉的师傅,师傅门下弟子众多,但田艳波是惟一一个学得师傅全部手艺的人。在西安给城里人做了三年家具,田艳波是充实的,也是心酸的,“虽然学会了做城里人用的家具,开始有了自己的收入,但很少有吃饱饭的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地人,能拿到的粮票很少,最重要的是,经常有管事的人儿来查,要是被查到就要被送回老家,几年里,感觉一直是在躲避中生活”。
1975年,经熟人介绍,田艳波起身前往郑州,在河南省纺织机械厂木工组里当起了工人。从一个流浪的木匠变成工厂工人,田艳波的心总算感到了一丝安稳,初入木工组,从钉设备货箱板子开始,田艳波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木工人员的素质,很快被分到了木工组做家具的队伍中,开始给工厂下边的宿舍和宾馆做家具,这让田艳波练就了一辈子从事家具制造工作的基础。“木工组制作家具的队伍时常超编,为控制人数,领导每几个月就会举行一次比赛,谁做得又快又好,谁就留下,经常排在后面的人就被送走。”前几次比赛,田艳波还不算出色,后来几次,他总是排在前几名,成了组里非常出色的木工。“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一个月能拿60多块钱,相当于国家规定的四级工的工资,领导特别欣赏有技术的人,所以那一年我过得很开心。”
在工厂里为宿舍、宾馆做家具是比较规律的,任务量也大,这除了让田艳波练就了一身本领,也让他对打制家具有了些新思考,“那时的家具造型非常简单,到现在人们还能在某些老房子里看见那个时代的家具身影,最多的就是‘文件柜一头沉’”。田艳波指着龙顺城技术科办公室内放在角落里的一个文件柜对记者说,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最流行的家具,一般比较宽裕的家庭或有身份的人家要打家具,或者是工厂为某些单位批量打制家具,必然会选择这样的文件柜,如果再要配上一张书桌,那就一定是“一头沉”,就是一边有抽屉,一边只是桌子腿的那种书桌。“经过打造者几年的思索,家具在款式上有了一些变化,而且在种类上也稍微丰富了一些,出现了高低柜、小衣柜、五屉柜等家具,这些家具款式曾风靡一时,现在在一些单位的老房子还能看见这样的家具。现在回头看看,那些样式能十几年不衰,跟人们的信息相对闭塞有关。”
返京待业——创业得到家具厂赏识
1978-1990年,外企进驻带来设计风潮
1978年2月,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严寒逼人,田艳波离开郑州来到大兴安岭一年有余。当时的田艳波有两个“一生的梦想”,一个是去南部的热带雨林,一个是去北部的大兴安岭林区,两个地方都有丰富而珍贵的木材,这对一个木工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源。离开郑州的时候,田艳波试着先往南走,但走到安徽地界,那里的方言他就基本听不懂了,于是当即掉头北上,到了大兴安岭地区。在大兴安岭的一年多时间里,田艳波感到无比的惬意,每个月他可以仅凭打家具就赚得300多块钱,这相当于当时一个省长的月收入,周围还有一些欣赏他的朋友在照顾着他。“那一年多是我最自豪的岁月,我时刻感觉自己是个有钱人!”
虽然在外面游刃有余,但每到过年的时候,田艳波会觉得很苦涩,家家亲人团聚,而他只能在街角火车站里徘徊。但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1978年年末,父亲被允许回到北京,随后田艳波便回到了北京,成为了众多待业知青中的一员。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田艳波没事就往天坛街道劳资科跑,问问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最后工作没等到,倒是与劳资科的工作人员及一些从全国各地返城的知青熟悉起来,直至组建了一支木工队接零活打家具,“那个时候每个月也可以收入300多块钱,日子过得挺好,还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说我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坐在家中等饭’的好模范,北京电影制片厂专门针对我们的事迹做了‘创业模范待业青年’的新闻报道,引起了一阵好评,木工队从最初4人发展到28人”。
技艺娴熟的田艳波引起了一个“奇怪老人”的关注,每次田艳波干活的时候,他总是远远地蹲着看,看了两个多月,老人走过来问田艳波愿不愿意到北京硬木家具厂工作,提到“硬木家具厂”,田艳波的脑中马上闪过“有好木料”这几个字,作为木匠的田艳波对木料的偏执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但他并没有马上答应老人,最后老人承诺“如果你来就让你当工厂画线的”,在这样的诱惑下,田艳波兴奋地到了北京硬木家具厂。“画线的是木匠中手艺最高的,俗称‘掌作儿的’,是工厂生产车间里‘领头的’,只要在来料时画上在哪里打眼,打多深,其余的就分配给其他木工做。”看中田艳波的老人就是北京硬木家具厂机加工部门主任,在画线的岗位上田艳波一干就是7年。
这7年让田艳波对家具设计有了更深的思考,什么样的样式更美观、更省料,能让家具结构更稳定,对工厂里每个新到的家具图纸,田艳波都会目不转睛地盯上半小时,他在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去设计这个家具”,设计的概念在那几年中时刻在田艳波的脑海中闪现。1987年,田艳波的职位从一个“画线的”变成了“出样的”,身份从一个工人变成了技术人员,被工厂派到外面参加“家具制图培训班”学习,从此成了北京硬木家具厂里的头号设计师。“出样的,就相当于一个大掌柜,客人描述要什么样的东西,你得能给画出来,然后再叫徒弟们去做,大掌柜的经验全凭亲手操练积攒起来的。”
正是田艳波走上“出样的”工作岗位的那几年,中国家具制造领域开始有了“设计”这一概念,田艳波也就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称得上设计师的群体中的一员,开始对设计有了更多的追求。“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国外企业已经进驻中国,对当时中国的城市生活起到了不小的改变作用,这对家具设计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大大小小的家具展销会上你会发现,家具款式设计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家具生产上开始使用五金件,这对家具设计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古为今用——钻研明清家具技艺
1990-1997年,家具式样越来越洋气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家具制造领域迎来了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时代,广东、浙江等地产的家具输送到全国各地,家具不仅价格便宜,款式更是新颖多样,多数款式是老百姓以前从未见过的,百姓居室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得益于大型工厂化生产的家具制造企业从国外引进生产设备的同时,也一并将国外的家具款式直接“引进”,家具制造企业在设计上完全奉行“拿来主义”,这无论对工厂还是对百姓,都是一个不错的举措。
新兴的工厂化生产的家具制造企业对老牌的国有家具企业造成的冲击不小,田艳波所在的北京硬木家具厂在1993年更名为北京龙顺城中式家具厂,生产重心转移到了古典红木家具制作上,继承了“龙顺城”这一明清家具老字号招牌,田艳波开始大量研究明清家具的制作技艺,与实行“拿来主义”的现代家具制造企业相比,龙顺城和田艳波走上了一条通往艺术殿堂的艰难道路。
在研究明清家具的几年中,田艳波对家具设计的思考变得复杂起来,想要再现明清家具的真实风貌,必须见到大量的明清年代的真品,但这些真品只有倒卖古董家具的“倒爷”才见过,而他们又不会制图;研究古典家具的专家学者对明清家具风格和雕工技艺会有准确的鉴别能力,但他们没有实践,做不出来家具;拥有绝佳技艺的匠人们一代代故去,他们的手艺逐渐失传。要想制作出韵味十足的明清家具,不将这些“权威人士”聚集起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将明清家具的精髓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
田艳波在明清家具研究道路上的苦恼没有对现代家具制造企业的飞速发展造成丝毫影响,行走在设计“拿来主义”道路上的现代家具制造企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销售高潮,生产企业数量也在几年之中向千位数字迈进。
专职设计——追求中西结合的风格
1998-2009年,市场对原创设计需求强烈
大量的家具生产企业为城市和乡村的居室生活添上了亮丽的色彩,1998年前后,随着住宅房屋商品化,人们强烈改变居室生活品位的需求催生了大量家装公司的出现,由此“家居设计风格”这一概念浮出水面,人们对家具设计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也正是这一时期,部分大学专业中出现了“室内装潢设计”这一专业,这说明家具生产企业对设计的需求已经十分强烈了。
看到了家具销售受制于家具款式设计,家具生产企业老总开始频频造访国外家具设计博览会,将国外的样品和新品家具宣传册带回国内,依葫芦画瓢地照样生产,由此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国外家具设计展禁止中国人入内”的不光彩事件。中国家具市场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大批国外家具生产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1999年,田艳波带着多年对中国古典家具设计的研究成果离开了龙顺城,到了一家在中国设厂的瑞典家具生产企业从事家具设计工作,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田艳波成了公司的设计主力,多个设计作品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赞扬,由此得到公司老板大为嘉奖,“公司的很多大客户都是响当当的跨国公司品牌或各国驻中国大使馆,我们要为他们设计所有的办公家具和各场所用家具,通常我们要给出他们一个中西风格结合的设计方案,这样既符合这些公司的国际北背景,也适应了他们立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田艳波的成功说明市场对家具原创设计的需求是十分强烈的,也就是说,家具设计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意识到家具设计价值的中国家具制造企业已经开始愿意在设计上加大投入,近几年来,驰骋中国家具市场的曲美家具频频与国际设计大师接触,付高额设计费请他们为曲美设计家具,曾有国内家具厂愿意出30万元购买曲美家具的设计图纸,但曲美家具并没有卖掉自己的设计作品。就连老字号天坛家具也开始花巨资邀请国外设计师担纲设计,使产品系列极大丰富,一改往日单一沉闷的设计格调,出现了美式、中式、现代等多个风格的系列产品。
2001年重新回到龙顺城的田艳波目睹了这几年中国家具设计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家具设计市场的强烈需求令田艳波感到欣喜。现在人们都追求生活品质,家具设计除了要满足基本需求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求与众不同。为此,田艳波也为市场不能培养和提供一批与需求同步的中国设计师而哀伤,“虽然大专院校提供了室内设计专业,但走出校门的设计师往往不能满足企业需求,因为他们太缺乏动手的经验,很多的设计只能停留在纸面无法落实到生产上,由此导致很多企业宁可花钱到市场上买成品拆了研究,也不愿意付费请设计师,企业的不付出造成了中国设计师成长慢,同时,设计师不肯潜心研究、难耐艰苦生活、抄袭成风也使其自身成长缓慢。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家具企业可以十分慷慨地为设计付费,而中国设计师也愿意为自己的名字负责、仅凭‘某某人设计’就能赚钱,到那时,中国家具设计就真正形成产业、走向成熟了”。